
宗教中国化有3个基本层面,即在政治层面的中国化、社会层面的中国化和文化层面的中国化。在这3个层面中,文化层面的中国化是最基础、最长远又是最深刻的中国化。各大宗教只有在文化层面尤其是在其基本信仰、核心教义和礼仪制度等层面,通过与中华文明的深入对话与互鉴互学,挖掘出各大宗教传统内部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和健康文明的内容,并对教规教义和礼仪制度作出有利于发挥宗教在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有利于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阐释,宗教中国化才能称得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对文化层面的宗教中国化进行探讨的过程中,有必要对以下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历史中,存在一个怎样的文化中国?在文化中国的形成过程中,儒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扮演着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说文化中国的形成遵循着一个“互鉴通和”的内在逻辑,那么各大宗教在其中经历了怎样的中国化过程?与儒家文明进行了怎样的对话交流?面向未来,各大宗教又该如何在文化层面坚持中国化方向,从而共构共建文化中国呢?
“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文化中国
地处欧亚大陆的东南部,先天的地理条件——北部的草原、西部的沙漠与高原、南部的崇山峻岭和东部的海洋——使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一个相对较为独立的文明综合体。然而,在这个文明体的内部,又存在着丰富的地理与生物多样性,不同的区域发展出自身的文明形态。从新石器时代直至夏商时期,在中国这片疆域上,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但表现形态各异的文明系统。它们散布于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灿烂、星罗棋布。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将其形象地概括为“满天星斗”。它向我们表明,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上,多样性、丰富性就是其显著特征。
“星斗”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在中华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共处于中国古文化的大系统之内,这些“星斗”形成了各具特色却又内在关联的文化区域。按照大致的分区,它常被分成6个大的文化区:第一,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区,红山文化为其代表;第二,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区,大汶口文化是其杰出代表;第三,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区,仰韶文化是其主体,在甘南的马家窑文化也表明它向四周的扩散并被广泛地吸收;第四,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区,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是其代表;第五,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区,它们构成楚文化的前驱;第六,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南方区。按照东、西、南、北的再分类,这6个区系又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南北各三区,或以面向东南海洋和面向欧亚大陆的三东南、三西北。在中华文明发展的长河中,这些多元起源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以各自的方式融入中华文明的有机体中。多元文明的相摩相荡,形成中华文明包容、吸收、转化其他文明的基本气质与内在逻辑。
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中华文明在东、西、南、北4个维度都进行着更为深入、频繁的多样文明互动。在西部,丝绸之路开通并日益繁荣;在东部,海上航行技术的发展使中国有了海上丝绸之路、瓷器之路和香料之路;在北部,草原游牧民族或以战、或以和的方式进入与农耕定居民族的深层次交流融合之中;在南部,山地民族也越来越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过陆地和海上的丝绸之路、瓷器之路和香料之路,在世界其他文明区域发源、成长的宗教也进入中国,进一步地丰富着中华文明的多样性。起源于印度的佛教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中国的僧人也通过海陆丝绸之路前往印度求法,佛教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伊斯兰教崛起之前,基督教会广泛分布于西亚、中东各地,它们也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公元7世纪的景教,可谓基督宗教中国化的最早尝试,其成就仍然值得今天的中国基督宗教深入挖掘。随着伊斯兰教的崛起,中东各民族也将伊斯兰教文明带入中国,并通过“伊儒会通”,使伊斯兰的信仰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入大航海时代,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在带来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将作为西方文明精神实底的基督宗教信仰体系介绍给中国士人,使中西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进入一个黄金年代。
在世界文明史上,绵延不绝、自成一体而又多样丰富的中华文明展现出个殊性。勿庸置疑,自然地理、历史道路等,都是造成中华文明一体而多样的原因。然而,从精神层面来说,中华文明的以下理念无疑值得特别注意。它们对于今天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并达致各宗教文明共同参与构建文化中国的局面,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坚持“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共同的人文精神包容、浸润并涵化多元宗教的基本理念。面对各种外来的宗教,中华文明不是简单地将其斥为异族信仰、外教或洋教,而是将其纳入“文化”的轨道,引导它们走上主动与中华文明对话互鉴的道路。在中华文明的根基处,对于“以人文化成天下”就有深刻的理解。按《易经·贲卦·彖传》的理解,文化并非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即所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通过对阴阳迭运、刚柔交错的天道运行的观察,古代中国哲人认识到世界是由彼此相异但又多样互补的各种要素组成的。人必须按照“天文”来制定或运行“人文”,所以“人文”的关键就在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就是按照人群自身的法则和规律,并采用“化”而非“力”的方式来治理天下,即尊重不同人群与宗教的多样性,以普遍的人文法则去教导他们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
坚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强调不同宗教的和平共处,并在互鉴互学中走向共同进步。中国哲人理解到“道”本身即意味着多样性。与其自然社会生态相适应,不同文明区域都有其所尊崇的“道”。万物最终的实在性,是某个单纯的“一”,但“一”本身处于自我否定和自我实现之中,辩证地表现为“多”。万物之源是“道”,道又在阴阳之中,正是在阴阳的矛盾互动之中,才生出纷繁复杂的万事万物。“道”是一个复数,这正是中华文明的智慧之源。表现为文化政策,就是各种宗教在中国都能找到其栖身之处,并在适应中国社会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互鉴互学中得以进步。
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为原则,坚持政治与宗教相分离,在保持政治统一的同时,使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得以繁荣发展。“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出于儒家经典《礼记·王制》。所谓“修”,就是人们可以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实践自己的宗教礼仪。不易其俗,就是不强行改变人们的生活习俗。“宜”就是按照当地情形的“物之所宜”。“政”是政令施为,所谓“齐其政”就是政令的统一。“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理念,正反映出古代中国从“满天星斗”向政治统一过程中的文化智慧。后来,当更多的民族与宗教不断地融入中华文明时,这样的文明理念和结构不仅没有抛弃,反而在更广的层面上得到了实现。
多种宗教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不仅能够存身,而且能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中,在与其他信仰传统的互鉴中,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中国佛教、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基督教和中国天主教,都呈现出被中国传统文化浸润和涵化的特点。这种现象或可称为中国宗教的“互鉴通和”模式。而这种模式之所以能够成立,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儒家的特殊气质。
儒家:既有独特精神气质,又能容纳各宗教
虽然儒家作为一个派别,是由孔子于公元前5世纪创立,但孔子自己就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将自己视为周文化的继承人,而周又是对夏、商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孔子本人并没有创作儒家之“经”,而只是古代经典的编修与解释者。儒家的经典体系,可以追溯到中华文明的源初之始。因此,儒家既是文化中国的精神成果,又以它的独特气质与制度延续,捍卫着中华多样文明之互鉴通和的基本格局。要推进我国宗教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从中华文明中接受浸润与滋养,理解儒家的这一独特气质尤为必要。
首先,儒家是一种具有精神性向度的人文主义。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杜维明在2014年曾提出,儒家是一种精神人文主义。这个概念标记着儒家在宗教问题上的“居间性”。它是一种人文主义,以此世维度的“仁”为枢纽,以“自我”为核心,在4个维度即己(自我)、群(社群)、地(自然)、天(天道)上展现出人性的丰满。就此而言,它区别于以超越性的他者为中心建立的宗教系统。但它又不同于工具性的、世俗的人文主义,因为后者将人限定为理性的、此世的存在,在现实中又常常发展出反宗教、反灵性的倾向。作为一种“精神的”人文主义,儒家承认人的精神,重视天人之间的相关性,它的人文主义理论与秩序是在向超越的神性开放与对话中建立起来的。在几千年文化中国的长河中,儒家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理性的,却不排斥对神圣天道的追求与思考。它是温和的,却勇于并善于以各种方法消化极端思维。正是它所具有的这种精神人文主义特质,使它既对中国本土的道教信仰,又对源于异域的佛教、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展现出巨大的包容性、开放性。一个儒者可以出入于释、道之间,甚至成为一个基督徒和穆斯林。这种特质,使儒家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去接纳并导引各种外来宗教走上中国化的道路。
其次,儒家既是一个名词,又是一个形容词。说它是一个名词,是指儒家确为一个独特的精神实体。儒家具有自己独特成型的稳定经典体系,有自己的概念系统,有以“天”“道”“生生”等作为核心术语的灵性形而上体系,有以希圣希贤为目标的修养论及工夫论,也有以传承儒家理念为己任的知识阶层。我们不能将儒家约化为仅仅一个哲学或知识系统。但是,儒家又展现出巨大的开放性、包容性和人文性,它几乎可以作为所有宗教的形容词而出现。换言之,可以有儒家的道教徒、儒家的佛教徒,还可能出现儒家的穆斯林、儒家的基督徒,亦存在深度认同儒家精神理念的犹太教徒和印度教徒。当人自称为儒家时,并不与他的宗教身份相矛盾。作为形容词的儒家,为宗教中国化提供了广阔的文化空间。
最后,儒家既呈现悠久的稳定性,又在与其他宗教的互动中不断调适自己,表现出鲜活的变易性。儒家发源于中华文明的原始时期,又贯穿于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之中。它的基本结构、精神气质、核心术语都是稳固的。但是,在面对不同文明或宗教的挑战时,儒家又不断与挑战者互鉴互学,吸收其他文明的精髓,并不断返回自己的本源处,挖掘自身内含的潜质。最显著的情形就是儒家在宋朝时期的大转型,以致于可将宋朝兴起的理学称为“新儒学”。在面对佛教、道教的挑战时,理学建立自己的形而上体系,沿着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衍生出深刻而系统的新思想体系。儒家勇于变革的精神,甚至体现在理学对儒家经典体系的重新修整上。它从《礼记》中抽取《大学》《中庸》,并与《论语》《孟子》组合在一起,形成“四书”,并置“四书”于“五经”之前,形成所谓“四书五经”。就儒家的经典体系而言,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甚至《四书》已凌驾于《五经》的地位,反映出儒学在与佛、道教的互鉴、论辩和互学后的变革与新风。可见,在向多元宗教保持开放和对话的过程中,儒家也在不断实现对自身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乡村振兴陕西网
乡村振兴陕西网 陕西鹏翔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鹏翔茶业股份有限公司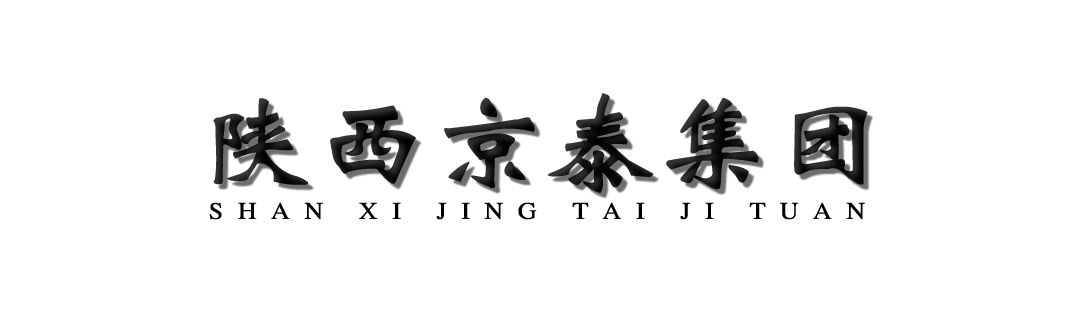 陕西京泰集团
陕西京泰集团 陕西省榆林中学
陕西省榆林中学 韩城市热力有限公司
韩城市热力有限公司 榆能集团佳县盐化有限公司
榆能集团佳县盐化有限公司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睿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陕西睿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陕西大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大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汉中勉县尧柏水泥有限公司
汉中勉县尧柏水泥有限公司 华阴市华西镇人民政府
华阴市华西镇人民政府 洛南县人民法院
洛南县人民法院 咸阳市商务局
咸阳市商务局 安康阳晨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安康阳晨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安康市满意建材市场有限公司
安康市满意建材市场有限公司 咸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咸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商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商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铜川市新区管理委员会
铜川市新区管理委员会 南郑县电子商务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南郑县电子商务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西安标准工业
西安标准工业 西安铁路局阎良工务段
西安铁路局阎良工务段 陕煤集团神木柠条塔矿业公司
陕煤集团神木柠条塔矿业公司 咸阳渭城中学
咸阳渭城中学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铜川市支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铜川市支会 神木汇森凉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神木汇森凉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宝鸡市科学技术局
宝鸡市科学技术局 咸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
咸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 西安凤巢网络
西安凤巢网络 CCTV列车频道
CCTV列车频道 西安牛皮癣治疗
西安牛皮癣治疗 西安轻质抹灰石膏
西安轻质抹灰石膏 西安水处理设备
西安水处理设备